
酒徒,走徒
Writer: 沐羽、陳子雲、Kris Li 李宗泰
浸大人文學課程30週年專題創作
沐羽、陳子雲、Kris Li 李宗泰
沐羽
來自香港,現居台灣。已出版短篇小說集《煙街》。清大台文所碩士生,一八四一出版社編輯,香港文學館媒體〈虛詞.無形〉編輯。獲文學獎若干,文章見網站:pagefung.com
Muk Jyu, from Hong Kong, now lives in Taiwan. He is a master student of th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Editor of 1841 Press, Formless.P-articles (The House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Literature Awards winner. Works can be found: pagefung.com


陳子雲
專題記者,現任職外國媒體。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於各文藝雜誌發表創作。長期專注電影評論,散見台灣及香港媒體。金馬影展第五屆「亞洲電影觀察團」成員、第二十六屆香港IFVA公開組評審(初選)。
Feature reporter, currently working for foreign media.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Creative Writi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published works in various literary magazines. He has been focusing on film reviews, and has been scattered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media. Member of the 5th "Asian Cinema Observer" of the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 and the jury of the 26th Hong Kong IFVA Open Category (Pre-selection).
Kris Li 李宗泰
見證人文學從課程升格為學系的一屆畢業生 (2014)。
數年前渡日深造,在溝通不良的時代學習溝通不良的美學。
Graduate that witness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umanities Programme into the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Creative Writing.
Went to Japan for further studies. Learning the aesthetics of miscommunication in the miscommunicative generation.

〈斷片在浸大橋上〉
我不喜歡一個人喝酒,關於喝酒的記憶總有一群人在場。在橋上,在公園,在尖沙咀,在打邊爐的所在,或者現在隔著電腦螢幕。
我不是不知道酒有一個同音字,喝酒的當下沒有人會搭理那個字,到沒有人喝酒時,才發現我們都被那個同音字掌控著,保管著。人都說:「尚有時間」,但一部德語電視劇裡時空穿越的悲劇說,「人正正身處時間之中,談何擁有時間?」
喝酒的人都走了。也不一定要走到他方,甚至有些人走到我看不到的只有一格窗戶見光的所在,走到任何看不到的所在,就是走了。
人還沒有走的時候,我們在浸大橋上喝了一整晚酒。站在2022年回望2013年,人沒有走,也不懂喝酒,胡亂把Vodka溝入橙汁可樂各種汽水,Whisky一喝便覺嗆喉得要命,也吸煙,那時我沒煙癮,只是個出沒社交場合的煙客。那時候Kris和他女友仍然一起,現在他們分開了,Kris一個人在日本;Christy好像也在,她也是一個人到日本留學,好久沒聯絡了。也有幾個當時的學生會內閣成員來到,當中一個女生Angela後來當模特兒、拍廣告拍電影紅到發紫,候選內閣在宿舍樓下派傳單時,Angela的美貌令大多數住宿男兒奔走相告,紛紛跑到樓下偷看。還有後來去了雲南,又回來香港當甜品師的Tempo,那晚我記得她喝得太凶,在早上嘔吐大作,居然要呼召救護車到場接走她。
我記得他們去了哪兒,然而我記不起那晚我去了哪兒,我斷片了。人生第一次斷片的感覺就是一片空白,酒勁愈喝愈從肚子往上湧,湧到腦門,本來不太能坐直的身體像被一股力量往後拉。時針過了凌晨十二點後往下走,我也往下倒,整個人被軟綿綿的石屎地吸引,牢牢地釘在地上不省人事,唯一記得是Page那個仆街仔不知發甚麼神經,吻了我一下確認生死。人聲仍然吵鬧,話題早已轉了幾遍,之後發生的事情我都不記得。醒來時,我正躺在宿舍樓下,是他們叫醒我吧?有人說我斷片下向宿舍入口閘機發起衝鋒,「撞閘機呀屌你」,有人哈哈大笑起來。
我問,都不用找我了?浸大橋到宿舍那一段路程要過馬路,我說不好就被車撞死。有人發表目擊報告:「你本來一直躺在地上,突然間你起身跑到浸大橋下,好像跳了陣舞,我們都在笑你,之後就不知道你哪去了。」又響起一片笑聲。
我去了哪兒?這次一生人一次的斷片是我大學時期的一個謎,沒有人知我怎樣走,我自己也不知道,斷片的時空裡沒有夢,沒有任何事物存在,像被削除的那一晚下半夜的時間,我怎樣也找不回來。
How did i get here?此後酒局一場接過一場,雖然我沒有再次斷片,但是那個疑問隨時間推移卻沒有消失,一直都得不到解答。不知道酒局的其他人是不是也抱著這個疑問,前往他方。
〈延長賽〉
那時我們年輕、無憂、佯作憤怒。那時仍然堅硬、強勢、堅信二元。
那時肺仍未痛,可以一根接一根地抽八號;胃也能扛,一杯一杯地喝爛酒。
但如果按照常理所說,大學時光是無憂無慮的最後樂園的話,我們經歷過一四,也經歷過一六。
人生被揉成一團,被丟出去,穿過喪失記憶的酒局,狼狽地降落到後來的位置上。
大部分的事情我都不太記得,但畢業後我們仍然經常回到浸會,繼續喝酒。爬上浸大橋,又或躲在宿舍後面的小巴站。
我們沒有甚麼必要回去,但可能是始終不捨得動身。
我們還在學生會室組了個讀書會,昆德拉的《無謂的盛宴》。一本爛書。但書名就是我們在做的事。
我們沒有好好長大。
我們拔苗助長。
寫了些詩,覺得自己很前衛。反對抒情傳統。
我們假裝自己已經成熟,穩重,看透某些事情的核心。
我們一字排開,從浸大橋頂向下撒尿。
我們習慣說「事情就是那樣」。
裝作窮、裝作不是很窮。
我們找了些相類似的工作。
我們相繼從同一家公司辭職。
以今天的說法來說,從這家公司「畢業」。
煙越抽越淡,開始學喝威士忌。
用電動牙刷,每日拉筋,買好的而非多的衣服。
不再憤怒,不堅硬,不強勢。
一四、一六、一九。
一九年後。
後來我還上了一趟浸大橋,不再爬上橋頂,就蹲在樓梯。
離開時帶走空瓶,多年來第一次。
像清走路障。
我始終也是沒有甚麼必要回去浸會,畢竟不是甚麼有歸屬感的地方。
如果真的喜歡它的甚麼,也只有幾個裝潢得很誇張的漂亮廁所。
至於學系,我能翹的課都翹了。
無法假裝對學系關注的議題感到有興趣:食物書寫?那是甚麼東西。
那是延長賽,無憂無慮的最後樂園:在學院裡,飲飲食食,慣性失戀。
畢業後我們特地回來對AAB外面那根柱子撒了泡尿,那根東西才剛蓋好一天。
我們叫它陽具。
後來我們不再憤怒。
後來安安穩穩。
後來發現我做行政還蠻拿手的。
放棄寫詩,從第一人稱過渡到第三人稱。
胸悶、喉嚨痛、牙痛、坐骨神經痛、胃食道逆流。
不隨地小便。就算是為了藝術也不。
瞧不起前衛藝術。瞧不起淺薄的詩。
二○年。二一、二二。打三枝針。
後來回不去香港。
沒有甚麼關係,我帶著香港走的。我是路障本身。
路障沒有記憶,它卡在中間。
〈包裝紙〉
在香港的時候,總說不出香港是甚麼,有甚麼。
這裡的人會說香港是九龍寨城,蝦餃燒賣。
示威也是土特產。
菠蘿包則是台灣的,然後又有人說要菠蘿包重光。
他們不知道的有:威士忌派對是種名物。
最少酒度四十的威士忌,雖然是烈酒,也是著名的派對酒。
桌上放著最少十支大家未喝完,
一個人也喝不完的威士忌。
沒有第一杯一定要從啤酒開始的習俗,
全球人均擁有最多日本威士忌的地方必然是香港。
「響」、「白州」、「山崎」用廣東話讀酒名,
比起用日文訓讀讀正音更有異國情懷。
你知道桌上放著Octomore 7.3的肯定是潛在的富戶,
喝著帶花香的,帶海水味的,
從未像那刻更覺得這地方是大英帝國殖民地,
蘇格蘭與愛爾蘭就在旁邊,
日本流行波本,他們不肯承認。
他們不知道的有:我們愛用很多理論說完一句話,
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形式主義、極權主義。
技能樹被全部點開,全部都是等級一,
只要技能夠多就似乎能夠頂著逆風,
社會主義鐵拳,資本主義鐵拳,
民粹主義鐵拳,國族主義鐵拳,
過家家的防護罩,
我有時會想像當時畢業之前都沒有開課的「人文主義」,
那節課就不談那麼「後」的事情了,
我們畢業之後有很多很「後」的事情,
後分手,後窮困,後運動,後離散,
後現代,後殖民,後馬克思,後人類世,
我們總會知道,不需急於一時。
他們不知道的有:我看《千與千尋》最少數十次。
把翻版DVD讀到跳帶,
那時候我基本上不懂日文,
「賑早見琥珀主」
原來離家三分鐘路程的那條曝曬了二十年的明渠,
也配擁有祂的名字。
湯婆婆手下的白龍,
與作為那條河的白龍。
他們不知道的有:我們需要把倒錯的溫柔倒轉過來。
花言巧語的人,訴說著美好願景的人,只相信自己百分之十的話。
不信也許是惡意,但更多是他們無法履行這麼大的話,
就像書本中的理論。
約定的前奏是做完愛的床榻,喝到爛醉的酒樽,還有用後放回原位的掃把。
記住誰把你沒有收拾好的碗碟放到星盤。
這裡會說香港是九龍寨城,蝦餃燒賣。
示威也是土特產。
我會加上慣用句:他にもあるよ。還有其他哦。
至於菠蘿包,你喜歡吧。

.png)

%20(1).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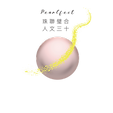%20(1).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