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客問〉
跨越中港台時空的廣東歌研究
胡又天的既古典又流行的角度
浸大人文學課程30週年專題創作
胡又天博士(胡逆天)Dr. Hu Youtien (Hu Nitien)
胡又天博士(胡逆天),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碩士、香港浸會大學人文與創作系博士。
精通中國傳統文化,學術研究範疇為華語歌詞。胡博士既是歌詞研究學者,也是詞人和作家。創辦同人社團「恆萃工坊」,主編《東方文化學刊》。
Dr. Hu Youtien (Hu Nitien), Bachelor’s in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Humaniti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Master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r. Hu is an academic and focuses on Chinese lyrics research, also a lyricist and writer. He is also the founder of “恆萃工坊” and the chief editor of 《東方文化學刊》.

訪問日期︰2022年8月17日
受訪者︰胡又天博士(胡逆天)
訪問︰Gloria Lam 林雯茵
紀錄︰Idy Lam 林歡曉
G: 你在香港住了多少年?想念浸大校園嗎?
胡︰3年。2011至2014年。我的情況比較特別,我一開始是在中文系,導師是朱耀偉老師。第三年的時候,朱教授去了香港大學。於是安排我到人文及創作系跟周耀輝老師。想念校園的是,我住在吳多泰中心,早上或中午,我可以走到九龍城吃飯。
G︰兩位老師很不同,但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特別是研究廣東歌。
胡︰對,我們都是研究香港流行歌曲。
G︰為什麼你想研究廣東歌?為什麼不研究台灣歌?
胡︰只要是華語歌我都有研究。從2001年大學一年級時我已經有興趣了。而且我自己都有寫歌詞。2010年我考博士班的時候,已經決定用歌詞研究為題目。當時我已經收集了很多相關的書籍,看到香港的研究水準最高。讀了朱耀偉老師的書後電郵他,當時他在浸大,我接受了他的建議,申請香港研究生計劃。
G︰你跟朱老師相處那兩年是怎樣的?那時你已經有一定的社會經驗,回到校園的感覺如何?
胡︰我當時並沒有什麼工作經驗,在台灣,大學畢業後的男生要服兵役,服完兵役才去北京做研究生。唸完碩士回到台灣亦沒有找什麼工作,只在家裡寫東西,之後才來香港讀書,心態上還是學生。
一般而言博士生會有找題目的困難,但我的研究題目從開始便確定了。當時研究流行歌詞還未有很多成果,我很容易做出與前人不同的研究。在這種情況下,跟朱老師的交流很輕鬆愉快。而且他不用從頭帶領我,因為我已經有相關學術寫作的訓練。有趣的是,朱老師說他也不知道為何被分配入中文系,因為他是讀比較文學出身的。而我的路數較接近傳統中文系的古典文學,詩話詞話,跟朱老師的招數不一樣。我走的是比較傳統的路,但又跟傳統不太一樣,西方的文化研究學派的心法我也有應用。
G︰從朱老師到周老師,他們的性格啊,研究方向都不一樣……
胡︰(笑)我跟周耀輝老師的路數也是相差蠻多的。周耀輝老師到荷蘭讀書就是讀文化研究;他年輕時打的底子跟我相差更多。他的創作關注各種邊緣的人群、幽微的情感和飄忽的世情,這些我也能理解。但同時我了解自己可以做更多正統的東西,因為我明白傳統中國文化的道統,知道保守派是在想什麼,幾十年來又是在失落些什麼。
接傳統的棒,鑽研中華歷史
G︰你說正統這個東西,你那麼年輕,而你又對傳統的那麼了解。你研究歌詞好幾年,當中是一種過渡、evolution,還是有衝突?
胡︰都有。我生在1983年,上小學時正好是台灣解嚴,社會走向開放之路;但學校內的規訓仍未完全放開。我正好就是在威權解構中的社會成長起來。舊的東西,正統派、保守派講的復興中華文化論調還沒有退潮。到了我中學時期才退潮的。
開放後,所謂的一綱多本的時代,往後學生的思想、接觸到的潮流就大不同了。在我之前一兩輩的台灣人,對現狀不滿者,大都是以對抗傳統的思路,去讀洋書、搞運動,來完成自己成長和學術上的啟蒙。也有少部份是真心認同中華正統,但後來就失語了。
我們這一兩屆的人夾在中間,還可以接受傳統的尾巴,對下一時代好的不好的改變都有所感。青春期的我雖然不喜歡傳統的威權、僵化的積習,但我更反感要全盤推翻的論調。所以我在叛逆期,反而是想要把中華傳統的東西——古典文學、諸子百家思想——學得比課本寫的更精,了解到更深。之後我便考進台灣大學歷史系,修中國古代史、近代史、思想史,碩士班再到北京大學繼續唸中國現代史,大概明白了這百多年來的思潮,各種形勢的變化。我就是這樣練出來的。
所以到我來香港浸會大學研究歌詞的時候,我已經有了從古代現代史到當代知識的儲備,更有了親身體驗——香港帶給我更多東西,因為香港中西交匯,又有本地的廣東文化,太精彩了。
G︰為什麼去北京呢?你要找最正統的正統嗎?
胡︰當兵退役後還沒找工作,覺得自己可以在學術上發展一下,繼續讀中國近代史,那時候也有很多台灣學生到大陸讀研究所,加上北京大學歷史系也是蠻有名的。我那一屆面試的時候,大約只有十位台生,十選四的錄取率還是相當高的。
G︰很有趣的經歷,但今次講回香港吧。你剛才說香港帶給你更多的東西,你可以具體講多些嗎?特別是在浸大的感受是如何的?
胡︰香港人的民族意識、香港傳統文化的承傳,相當高的程度是民間自發的。不管是南來的文人,還是本地的民眾,他們都是以自己的想法去發展和傳承文化,承傳與創新。這樣生長起來的文化就非常有魅力,沒有那種教條味。無論是檢討傳統古代思想的優劣,或發揚其中的精華,都是由民眾和文人自發。當中,不一定每一個都好,不一定每一個都對,但發得出聲。香港的報章雜誌曾幾何時特別發達,我在香港的時候看很多報章雜誌;其實十年前這行業已經在衰落啦,但前一個時代的繁華我還可以看到。
G︰你看什麼報紙文章?
胡︰《信報》、《明報》。我們宿舍樓下每天有《信報》。這個其實可以講一下:我父親在台灣的《聯合報》工作,他曾在1994至1995年期間調到《香港聯合報》。他從香港回到台灣後,又負責紐約《世界日報》的社論,而紐約《世界日報》又因為有很多香港人移民到美國和加拿大,他們關心香港的新聞。所以,《世界日報》社論就會講很多香港的新聞,請很多香港的教授來寫社論。我爸負責看這些,我會跟爸一起看稿子,改稿子。我爸在香港工作的時候,每個月回來一兩次,也會帶香港的書刊回來給我。後來又繼續訂香港的報刊。所以我十幾廿歲的時候,經常看香港的《信報》和一些周刊。跟大多數台灣人都不一樣,我比他們看多很多香港書刊。


粵語的韻味,學者的眼界
G︰說回你的專業,現在廣東歌又好像重生了。你來的時候有一點往下走,你覺得廣東歌精彩的地方在哪?
胡︰精彩的地方,在於廣東話本身的音韻,粵語九聲,那麼難填,但香港就是有少數人能做編作,把它填得那麼好,把這個語言的本身韻味都發揚出來。香港的粵語是漢語那麼多方言內,唯一一個能跟現代化進程的。有什麼新詞彙,國際上新的詞彙,廣東話都會與時更新。相對來說,雖然台灣的閩南語和客家話在2000年以後得到政府的扶持,但是客家話仍停留在農業社會,閩南語稍為前一點,但也只有進入到工業社會。在現在這個資訊時代,用閩南語和客家話很難表達現在很多的詞語。他們說到這些(反映時代的)詞語時,就會改用國語來說,或者是講不出來,或用英文。廣東話能與時並進,什麼(語境/場景)都可以應用到。所以,廣東話寫歌詞就什麼現代的東西都可以寫;同時傳統的東西又沒有完全丟掉。對於在乎語言和文學的人來說,這就是一個寶藏。
G︰你有沒有很喜歡的填詞人?
胡︰尹光。
G︰〈荷里活有間大酒店〉。
大家大笑起來。
I︰剛才你說客家話停留在鄉村的年代,是指?
胡︰例如你說「電腦」、「網路」,如果客家話要硬講也可以,但他們會覺得尷尬,因為不習慣。例如要說股票和金融,這些現代都會的用語,說閩南語和客家話的人都不習慣說這些。他們談到這些,就會轉用國語,大家習慣用國語來講。如果大家都講,講久了,那大家都習慣了。但是因為官方語言是國語,他們日常閩南語和客家話的使用場景又不講這些,便制約了它們的更新。
G︰問你一個個人的問題。過往很多批評說廣東歌情歌太多了,悲情的歌太多,你怎樣看這個?有沒有一些廣東歌對你愛情的想法有啟蒙或inspiration?
胡︰情歌氾濫在盧國沾的年代已經有批評。我們研究者會注重各種的議題,就算是情歌也會着重於現在的情歌跟以前的情歌有什麼不一樣。這幾十年的研究,非情歌在我們的研究比率也大大的提升。也許,情歌仍佔主流,但是在九十年代和千禧年代已經不囿於男女愛情的情歌。另外情歌翻來覆去,除了一些探討的議題講得特別好的以外,許多都不能出頭。反而非情歌容易觸及大眾當前在意的話題,就能風行一時。我剛來的時候是謝安琪的〈喜帖街〉,黃偉文作詞。同一時間還有〈陀飛輪〉,還有小克的〈一支得啩〉。小克把林夕的〈一絲不掛〉改成戒煙主題的非情歌,這些都流行一時,我們研究者和創作者都十分欣賞,香港廣東歌的活力就是在這裡。所以情歌氾濫的問題其實已經解決了一半,另一半是它在環境改變下自己消失了。
最近幾年Mirror,他們的歌表面上是情歌,用愛情來包裝各式各樣的勵志、安慰、撫慰人心的,情歌是一個殼,大家在乎的並不是愛情。
G︰他們很大膽……。
胡︰這也是時代的需求啦。人心都想要這些東西。現在,寫得再好的情歌,大家也不一定受落。我來的時候是廣東歌處於比較衰落的時期,大家對於長久以來的情歌已經有一些麻木。那時大批香港人北上拍片,感覺那時候大家都在撐著場面,撐著繁榮,那些TVB大台已經顯露老態。那時候有個持續蠻久的話題,亞視何時倒閉。(笑) 「亞視永恆……」那時候,我看了就笑。我查那歌詞內講的人和節目的典故,慢慢抽絲剝繭,幾十年的文化就像拼圖一樣,一片一片展現在我面前。
G︰最後,你願意再回來浸會大學嗎?
胡︰當然是願意回來講一些講座啦。

.png)

%20(1).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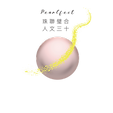%20(1).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