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學與我的時裝寫作事業
Writer: Christopher Lai
Editor: Idy Lam, Gloria Lam

浸大人文學課程30週年專題故事
黎偉麟 Christopher Lai
黎偉麟
2013年香港浸會大學通識及文化研究文學士畢業。現為《優雅生活》時尚寫手及編輯。
Christopher Lai
Christopher is a 2013 graduate of the Liberal and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me. He is now a fashion writer and associate editor at LifeStyle Journal.
小時候從來沒有想過「我的志願」是什麼,也沒有想過讀大學要修讀什麼科目。高中選科時,好友都選理科,也就跟大隊,放棄了也許會唸得更得心應手的文科(也有虛榮心作祟,理科班要求高分一些)。會考後那個暑假,媽媽終於安裝了家居上網,雖然比其他同學遲了6年,但神推鬼擁下也開始了時裝筆耕。再回溯小時候媽媽帶我到公共圖書館消磨時間,開始翻閱時尚雜誌:美國版《VOGUE》、《Elle》、《Cosmopolitan》、本地的《號外》和《君子》……省了上網的錢,結果沉迷了一個更花錢的興趣——時裝,也令我種下了日後時裝寫作事業的種子。
中學七年,不可說沒有用心,但讀完書考完試便過眼雲煙;真正喜歡閱讀的除了(已故)本地時裝作家黎堅惠小姐的時裝專欄外,也從她筆下提及的名字順藤摸瓜去讀:張愛玲、陳冠中、鄧小宇、邁克、林奕華、亦舒、梁濃剛、李志超、周肅磐……然後再從這些名字留下的線索繼續輻射般搜索其他與時尚有關的歷史、文化和icons。大量吸收時尚養分後的我寫作慾望萌芽⸺別人用Xanga寫日常生活瑣事的網誌或青春期的羅曼詩,我只想寫關於時裝的一些感想。我直覺以為要加入時裝行業,就必須讀一些相關課程。奈何高考成績平平,分數只夠修讀理工大學的時裝與紡織高級文憑課程。
高級文憑的兩年可說是我記憶中的黑洞,那些染布紡紗的實驗忘得一乾二淨(極可能根本沒有入過腦),snobbishness也讓我看不起不懂時裝、也沒有什麼「文化」的同學,而對學科毫無興趣的我自然也考不上學士學位,也有點輕微的情緒問題。僅有的記憶是在最後的期終考時,在圖書館碰見某同學,我向她流露了對考試的擔憂,平時不覺她成績優異,居然淡定自如;原來她已報讀浸大人文學系的「通識及文化研究」學士課程。看了課程簡介後覺得這似乎是「適合」我修讀的東西,可是截止日期已過。
那個「空檔年」,我繼續在微博發表關於時裝、流行文化的文字,竟也吸引到大陸雜誌編輯邀稿。我隱約發現,時裝寫作可能是我將來的事業方向。
2011年,我考進了浸大國際學院的LCS課程。最初只視這個課程是獲取一紙學歷的途徑,理想是能在課題中有些啟發⸺兩年下來的結論是,人文學科對我的時裝寫作影響甚大:一般時裝記者/寫作人的問題意識是「時裝問題時裝解答」,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忘記了潛藏在時尚之下的文史哲、社會學、藝術美學、各種思潮的底蘊。因為「支筆好」(前上司語),在2016年加入《香港01》後,以至後來在本地雜誌《MING’s》、國際雜誌《VOGUE》及《Madame Figaro》香港版等時尚傳媒都有較「好」的際遇。
「時裝新聞學 Fashion Journalism」在外國是一門學科,在時裝設計名校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就設有Fashion Journalism and Content Creation 一科。根據課程簡介,課程「將新聞技能和價值觀與核心時尚知識相結合,涉及最新的通信實踐和技術以及文化問題」,讓學生獲得「時尚和媒體行業工作所需的技能和知識」。或者我從來不視自己為傳統觀念上的「記者」(Journalist),也沒有正統新聞學的訓練,我從來沒有「記者」的包袱⸺做臥底調查、發掘真相、嚴肅批評……。
2013年《紐約時報》時裝評論人Cathy Horyn大力批評時任Saint Laurent創意總監Hedi Slimane的首作後,下一季就不獲邀請觀看時裝展。*面對品牌廣告商的壓力,99%的時尚雜誌都不可能對客戶作出真誠的評論。近年網媒《Business of Fashion》走收費模式,看似避免了廣告利益衝突與編輯自主的問題,但事實上奢侈品巨擘LVMH集團也持有此媒體小量股權,誰能保證當中沒有影響?「雞髀打人牙骹軟」是業內慣例,禮物就算不送給小編,肯定送到總編枱上,撰稿員自動變成「讚稿員」。唯一慶幸的是,時尚媒體的所謂「腐敗」倒不像政治或社會新聞,被美麗文字「哄逗」多買了一件不那麼美麗的衣服,最多浪費了一些金錢,��不至於構成什麼公眾利益危機,頂多是市容美學災難。
在這個時尚產業巨變的背景下,我大部份時間需要為廣告客戶策劃和編寫軟銷內容,跟我寫作旨趣無關,用馬克思的說法,完全是「異化勞動」。在香港主流媒體書寫時尚,就像劉以鬯等上世紀50、60年代的「寫稿佬」,為種種市場、趣味、權力和制度所支配,但肯定沒有《2046》中梁朝偉般有型。
某程度上,我是幸運的。
初入行時的《香港01》是大型網媒,大部分時尚品牌都不是常客,幾乎沒有過任何言論限制;上司也欣賞我的寫作興趣,容許我寫許多小眾題材,用一個名為「Style Reader」的欄目介紹關於時尚與閱讀的種種。不過,要數我最得心應手的時候是其後在本地雜誌《MING’s》開闢的的欄目「MING’s People」,每月深入《明周》資料庫發掘本地時尚偶像的珍貴照片,以時裝角度重新認識他/她的魅力,側面寫香港的流行文化歷史。及後加入國際雜誌香港版的《VOGUE》和《Madame Figaro》,商業壓力巨大,但優勢是有許多機會訪問任何你感興趣的人物,而且在「權威」的商標下,容易得到讀者的注目。
可是,我也是不幸的。
從盤古初開的第一天起,文字在時尚傳媒眼中是不獲重視的。除了上述因時裝客戶的無形壓力引起的「讚美壓倒批判」(這可會和寫手/編輯不自覺的自我審查,免卻麻煩有關?),行內人以及時尚雜誌的讀者,重視的都是以視覺出發的時裝造型故事(很討厭「大片」這個翻譯)。看《穿Prada的惡魔》真人Anna Wintour如何編輯美國版《VOGUE》的紀錄片《September Issue》,導演何曾關心過雜誌中任何一篇文章?全片關心的是時任時裝總監Grace Coddington如何拍攝造型特輯,Anna Wintour如何揀選封面照片。我面對的殘酷事實是,幾乎所有的老闆都認定我「寫得好」,依據對我本人的偏見和「功能最大化」的意識,總不會派我參與重要的拍攝工作⸺在外國嚴格分工的時尚雜誌工作,在香港卻通常是一人身兼數職,除非你視覺美感奇差,但我卻是死於「寫得好」。
跟大部份文字工作者面對的問題一樣,文字不值錢(價值是另一回事)。簡單一點來說,就是時尚造型師一個客戶工作的酬勞,很可能比時尚寫手一個月的稿費還要多**。一般而言,一篇600字網文是300至500元,能一個字收一元已屬幸運;但一份客戶的造型工作數萬元酬勞也是尋常事。工作性質當然有所不同,但寫稿��收入之低,就算不蠶食心靈,都肯定令人付不起香港高昂的租金***和時尚世界講究的裝扮行頭。處於這種「弱勢」,可能是我入行以來最大的一個陰霾。唯一的安慰是,講究Branding的時尚品牌,仍然未敢離棄文字(儘管許多傳訊和公關人員都是「文盲」),讓我仍可賺取卑微的生計,並在狹縫之中寫一點有趣的文章。
在Web 3.0新媒體時代下,文字書寫對於時尚的重要性進一步下降,很可能在比想像中更快的將來,我們再不需要用文字詮釋和理解時尚。這點從許多近年湧現的Tik Tok拍片者成為時裝品牌招攬的對象可知一二。
事實上,Fashion YouTuber通過頻道的貨金制度,重新找到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權,時尚評論似乎有了曙光。但對於尚在「建制」之中的編採人員,他們卻要為了演算法和社交網誌來寫content farm式的文章和拍影片,結果是被瀏覽率及大數據牽著走,製造愈來愈多垃圾內容⸺作為一個在香港成長,就算受到人文學「荼毒」而不致唯利是圖,為了生存也會照本子辦事的人,花點小聰明,數總是跑到的,但美學上的快感則是無限趨近零。
近日轉職到新的崗位,擔任一本本地布爾喬亞生活品味指南的副主編。回想過去16年時尚寫作歷程,當中有很多意識形態和經濟影響的糾纏、掙扎、交戰,更有無數束縛和限制,本人礙於性格及能力局限,縱有萬般不足,但自問已經盡力,只好釋懷。歸根究底,我只不過是個喜歡買衣服鞋子的人,也剛好愛上寫作而已。對於自己走過的路,我完全無悔——唸文科未必搵到大錢,但在亂世時或可讓人安然,比任何物質都更重要。
*“Hedi Slimane v Cathy Horyn: The story behind a fashion spat.” The Guardian, Guardian News and Media, October, 3, 2012. https://www.theguardian.com/fashion/fashion-blog/2012/oct/03/hedi-slimane-cathy-horyn-fashion-spat
**編按︰香港1993年一名助理編輯月入HKD12,000至13,000。 2013年, 一名初入行助理編輯月入大約HKD13,000至15,000。見Lam, M. G.. “The challenges of creative labour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printed to digital media in Hong Kong”.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okfulam, Hong Kong SAR.2017.
***編按︰根據星島日報 C29 新界睇樓王 (2001年11月6日) ,綠楊新村每呎租金14元。根據美聯物業官方網站( 2022年5月12日),私人住宅平均呎租約34.38元。見〈綠楊新村 兩房租七千全包〉,《星島日報》 新界睇樓,2001年11月6日,頁C29。見〈美聯「租金走勢圖」連跌6個月後喘穩 4月平均呎租回升約0.3%〉,《美聯物業》,2022年5月12日,https://www.midland.com.hk/property-news/%e6%a8%93%e5%b7%bf%e6%96%b0%e8%81%9e/%e7%be%8e%e8%81%af%e3%80%8c%e7%a7%9f%e9%87%91%e8%b5%b0%e5%8b%a2%e5%9c%96%e3%80%8d%e9%80%a3%e8%b7%8c6%e5%80%8b%e6%9c%88%e5%be%8c%e5%96%98%e7%a9%a9-4%e6%9c%88%e5%b9%b3%e5%9d%87%e5%91%8e%e7%a7%9f/

.png)

%20(1).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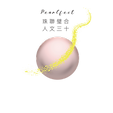%20(1).png)